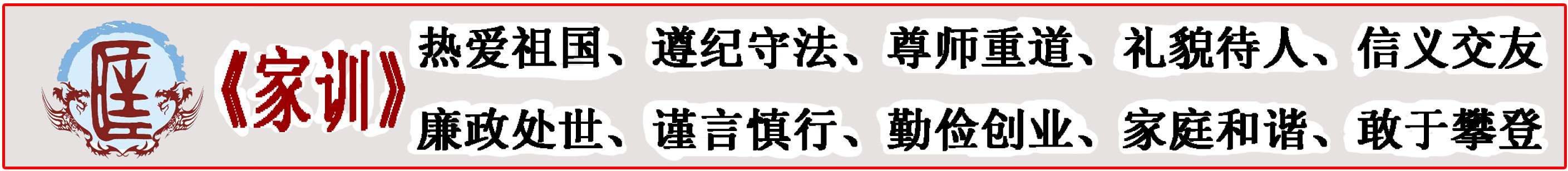
深刻的见地,平实的评论——读匡老评述儒家孔孟思想的两篇旧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匡亚明同志就多次提出应当对儒家孔子思想进行认真的再研究再评价,并亲自主笔撰写《孔子评传》以为示范。1985年初《孔子评传》一出版,立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与回应。此后,匡老又在许多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反复论述研究、评价儒家孔孟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深入阐发儒家孔孟思想中至今仍保有一定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八十年代后期,匡老更提出用“人学”来概括孔子思想体系的想法,既有研究视角上的新意,又有现实的针对性,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日前蒙匡老雅爱,惠赠新出版文集《求索集》一册,从而使我得以重温匡老近年来有关评述儒家孔孟与传统文化的许多精辟论述,更使我得以拜读匡老一生在文史哲政教等广泛领域中的灼见。其中,匡老一些早年的著述,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在这篇短文中,我仅就“学术编”中的《儒家哲理观——“中”》与《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两篇旧文谈一点感想。这两篇文章都写于1925年冬,那时匡老尚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十九岁),然而在这两篇文章中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是如此的深刻与平实,于当时来讲,诚可谓“后生可畏”也。不仅如此,我认为,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见解和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相当深刻和富有启发的。比如,在对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孔孟思想的问题上,当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青年,几乎无不对之持全盘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正如匡老在《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一文中开卷即指出的,当时一般知识青年的想法是:“我们觉悟了,那种无生气的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仁人君子,在这优胜劣败的竞争潮流中,决不再有他们立足的余地。”“那种萎蘼衰颓的劳什子(指儒家孔孟思想),还存有我们现在一噱的价值吗?”然而,匡老则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指出科学地研究儒家孔孟思想的必要性。他说:“我们且扪心一问:孔孟的学说是否都是废话?孔孟是否是中国目前致败的罪人?即退一步讲,我们即使承认孔孟的学说完全是废话;甚至孔孟诚然是中国的罪人;那么,我们依据科学的精神,也应当研究一下其所以然,考究一下它为什么,是否尚有改良保留的可能。就此一点,则孔孟的学说,终有够我们大大的探求一下,深深地揣摩一番的必要和价值;看看他们何以能负数千年的盛名,做中国式的——东方的——文化之中心。”(《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求索集》第13页)匡老发表这两篇文章的时间,也正是当时中国学术界讨论中西文化问题十分热烈的时候,所以匡老在《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一文的首尾分别引用了两位学者批评盲目崇拜西洋文化、学术,妄自菲薄东方(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论说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作出自己的回应。特别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匡老最后的一点补充,他说:“对此,我只作下列补充,即凡事出于本国人自己之手,好的必须保存发扬,不好的必须排除抛弃;凡事出于外人之手,好的必须吸收学习,坏的必须抵制弃去;这才是复兴中华,繁荣文化的康庄大道。东方文化的主人翁啊!你们忍抛弃所有的优秀文化祖产吗?”(《求索集》第32—33页)依据以上的原则和方法,匡老在这两篇文章中对孔孟学说中一些重要概念范畴所蕴涵的哲理进行了具体、细致而平实的阐释和评价,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与借鉴。《儒家哲理观——“中”》一文,篇幅并不长,还不到三千字,然对儒家“中”概念中蕴涵的哲理却分析得相当透彻。他分析了儒家“中”的哲理所包含的三方面主要内容,即“重天命”,“重内心自励”,“重保守”;并对“天命”、“诚”、“保守”等概念作了饶有新意的诠释。如对“天命”概念分析说:“我们也不应当以辞害意,以致把孔孟在这里所讲的既不左、也不右而适中的‘天命’和宗教上有人格的上帝之命相混淆。”“其实,孔孟重天命的缺陷,就在于含糊其辞,不明朗,没有能明确指出,‘天命’不是指一个什么‘神灵’在天上指挥自然界和人间社会一切事物的运行,而是指自然界和人间社会自身逐渐形成的运行规律,那就清楚明朗了。”(《求索集》第7页)总起来说,匡老认为,儒家“‘中’的哲学提倡听天由命,安分守己,放弃抗争,确实是一种消极的保守思想。社会要进步,要变革,就要突破这种思想,就要打破它对人们头脑的束缚。……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儒家‘中’的哲理在教忍如何困苦自励,如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方面,确有其合理的、积极的思想实质所在。在儒家‘中’的哲理中,前者应打破、清除,后者应保留、发扬。能如此,就可以在儒家‘中’的哲理中找到有益于当今的不少珍贵思想。”(《求索集》第10页)在《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一文中,匡老详细分析了“仁”包含的五个主要原素,即“亲亲”、“忠恕”、“诚”、“礼义”和“乐”,这里我就不再赘引了。但在这篇文章的“余论”中有一段专门诠释“孔子好古观”的文字,其中有些议论甚是发人深省,我觉得很有必要摘引出来,以供今人思考与回味。文章说:“有人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来反驳孔子,说他放弃创作的天性,只是好古,因袭主张。这种批评的人很多,他们都自认为‘自我的发现者’,一切事情都要拿‘自我’做中心,藐视一切古人。这种精神固是不差。但我相信短时期的‘自我’,和已往的纵的‘亘古’相比,真好似驹光过隙;一个‘自我’的精神思想,和古来千万个英杰圣贤的精神思想相比,真好似沧海一粟的精神思想,不问路径,不靠凭藉,而任‘自我’去发展,恐怕反不能跳出古人的精神思想的圈套呢!因为社会的进化,文明的兴盛,都是连续性的,逐渐的,即使外表上看去是突然变革,也是由来已久的结果,决不是一人或少数人之力所能突然造成。……所以无论什么伟人,都要拿已故的学说和成绩作一切改进的张本。若把古的一概抹杀,一切都要自己所创作的,那么最好是从‘茹毛饮血’的生活起。试问于事实上可能吗?”(《求索集》第31—32页)匡老这两篇文章的发表,距今已整整七十年了,然而至今读来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二十一世纪的即讲来到,又一次展开了有关东西文化的热烈讨论,此时此刻重读匡老的这两篇旧文,实在是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