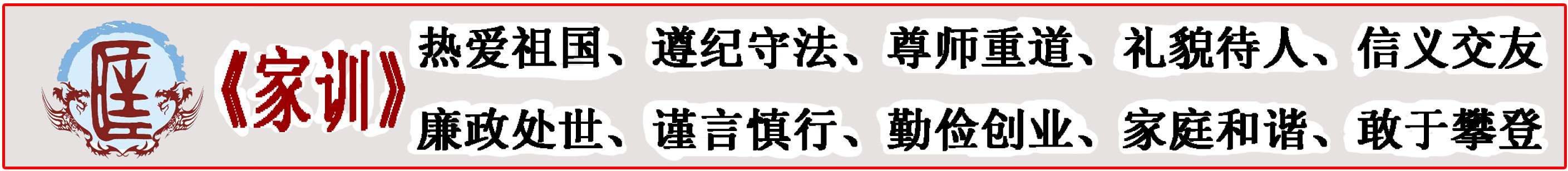
待到道光皇帝御批重审“漕案”后,都察御史指示“湖广总督会同湖南藩、臬两司调查审理”,此时随同递解至武昌狱中的甘启琇已经病死狱中,且先后刑讯致死或病毙的“漕案”人犯已累达27人之多。李逢彬很同情匡光文,为慎重起见,花了三日时间反复研究案件卷宗材料,发现要救匡光文并不难,只需匡光文不承认是一个人所为即行。而后,他亲自提审匡光文。
提审匡光文时,李逢彬见他果然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关押多时已然步履蹒跚,因此请匡光文坐下,并且启发他不必搞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
“先生揭发征漕弊端,本是为民请命。此后涉案人员多指先生为首,纵是不实,亦难辨真假。如今之计,只要先生一口咬定并非你一人所为,便可罪分多人,也便不至死罪。”李逢彬想救匡光文一命,给他出了这么个点子。
匡光文自然明白总督的好意,他微微点着头笑了笑,这才回答:“吾本意只是为民请命,这才触怒贪官,如今既不能免罪,又何必罪及别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吾不为也。”
说完,匡光文起来,走上前去,扶起管笔,在堂录的供词上写上“天理良心”四字。然后放下笔,朝李逢彬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李逢彬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叫衙役备办了一桌上好酒菜,亲自斟酒一杯相敬。
李逢彬对贪官污吏也不手软。
首先是那个金德荣,企图拉匡光文下水而未达目的,竟挟嫌报复,率营丁围捕匡光文,导致匡光文率众拒捕,实属无能之辈,光革职不足以警告后来者,请皇上批准发配新疆充军。钱臻身为藩司,专管一省人事,竟轻率判案,影响“政府”形象,应开缺交刑部重处。张孔言不明是非,烧毁民宅,拘捕过份,草菅人命,降级使用。其他审理此案不力的官员,都分别给予了处分。至于匡光藻、简开泰两人,劫持囚车触犯律法,发配新疆充军。此时匡光藻已病死狱中,充军自然是去不得了。
藩司钱臻最不服气,把自己“开缺”的气都发到匡光文身上。因此,李逢彬的判决是道光五年(1825年)九月上报刑部的,待刑部批下来,执行绞决也是来年秋天的事了。钱臻觉得像匡光文这样的人,刑部极有可能会减罪(不处死)执行。为泄私愤,竟在开缺尚未离任之前,逼迫臬司提前在长沙绞死匡光文。这一年,匡光文56岁。
得到匡光文已被贪官提前执行死刑的消息,家人即赴长沙备办棺木运回醴陵安葬。
从长沙出发,沿途百姓“祭奠号哭塞道”,一百七八十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一个月的时间。
匡光文为了什么丢掉了生命,黎民百姓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许多人继承他的遗志,要求减轻漕粮负担,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光绪年间为民请命者不绝,终于达到了目的,漕项减至1700文,贪官污吏收敛了许多……
名士作传 肝胆永垂青史
失之疏忽 史料一去不再
我要的答案仍然没有。
匡光文是醴陵人,醴陵县志会不会比《醴陵乡土志》记录更全?抱着这个希望,我专程回了一趟家乡,在县图书馆陈馆长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民国年间修的《醴陵县志》,从十多册线装书中又很快找到了《人物志》篇,不费什么力气便寻到了匡光文。一口气读完,谜底终究揭晓了。
原来匡光文死后,醴陵县同治年间重修县志,“乃无一字及之”。但百姓不忘他为民请命“义愤激发,历艰难险阻而不易其志,临难毋苟,视死如归,何其仁何其勇也”。道光六年(1826年)陈心炳任醴陵县令,他敬仰匡光文,特地呈请巡抚批准,从道光七年(1827年)开始,连续三年提取漕粮“奇零尾数”折二千余两银子追抚他的家人。百年之后,匡光文的六世孙匡弼追念先祖,花了一笔钱从晚清藩司衙门将匡光文“漕案”的全部卷宗买了回来,请醴陵反清志士、苏州《大汉报》主编傅熊湘为其作传。于是,辛亥革命后醴陵修县志,匡光文传记入选;傅熊湘编撰《醴陵乡土志》,匡光文彪柄其中。
醴陵山水养育的一代英烈,得到了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匡弼买回来的“漕案全卷”,当然包括英和等人奏陈并由军机处抄录的录副奏折。不然,傅熊湘作传时怎么会将录副奏折的部分内容写进去呢?而“漕案全卷”当然是包括漕案所有办案资料的,于是我后悔不迭,那日醴陵古玩商人地摊上那一大迭乱纷纷的纸片片,说不定便是其中的大部分,我却失之于疏忽大意了。
我能原谅我自己。谁能想象得到,170多年前的一个惊天大冤案,它的“全案”竟在地摊上零乱破旧的废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