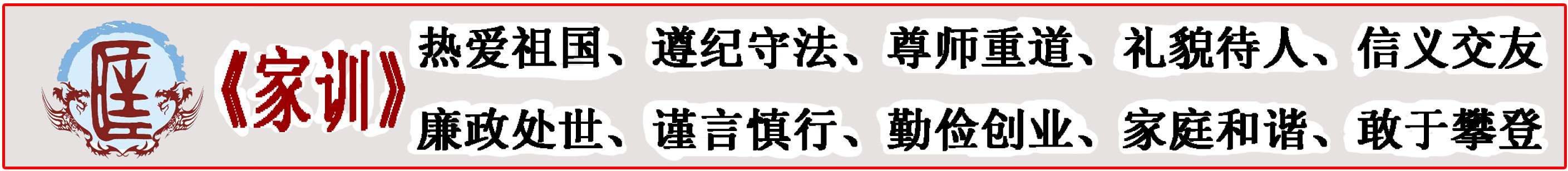
说孔入仕
孔丘请来了孟懿子,提醒道:“阳虎要动手了。”
“您怎么知道?”孟懿子不解地问道。
孔丘缓缓地说道:“阳越来请我为臣,允诺世代继承。世代继承,除了大主公,谁能给出这样的承诺?阳虎自己应该知道,只要三桓还在、大主公还在,他一个叛臣终归维持不了长久的,他这几次出征换得了百姓中的威望,这次回来,就要对所有人一起发难了。”
听了孔丘的这些分析之后,大家觉得很有道理。可是面对着阳虎和公山不狃的联手,大家束手无策。有什么办法控制他们呢?恰巧季平子家的车夫林楚来找孔丘,细数了阳虎的野心与精巧布局。
鲁国的君臣上下都收到了阳虎的邀请,孔丘与门徒吃饭时也怪异地收到一个烤乳猪,没想到,乳猪腹内也藏有阳虎邀请孔丘的竹简。孔丘无奈地摇摇头,自己天天讲仁义、解释礼仪,乳猪都已收下,又怎能失礼爽约呢?
不久,子路打探,公山不纽已经大兵驻扎在曲阜城外通往蒲圃的路上。孔丘连忙嘱咐孟懿子多招募些士兵,多准备些武器食粮。孟懿子也告诉孔丘,阳虎已出城去见公山不纽。
孔丘赶紧坐车向季孙府驶去,来到季孙府刚刚停下,不巧阳虎的车子驶了回来。这让已经下了车的孔丘感到吃惊。
“幸亏我出门不远,忽然想起昨天给你送乳猪的事情来。要不,怎么能和你碰上。见你一面真是难啊。”阳虎像是回忆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说来也真有趣,当年你盛装想进这个门,是我拦住你不让你进,可现在我请你进这个门,你却怎么也不来了。”
孔丘像是嘲笑自己,又像是嘲笑阳虎似的看了看季孙家的大门。
阳虎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听你说过,陪臣执国命,过不了三代。我希望这话不仅是因为那年的事情而说的。我没想过三代,你知道吗?我不会想那么远。这话吓不到我!”
孔丘轻轻地说:“我没想要吓到你。”
阳虎说:“你是看我囚禁了季桓子,还与三家盟誓,实际上现在鲁国国政竟然出自一个陪臣手里,觉得看着不顺眼,对不?季桓子好色、好财,鲁定公软弱无能,如果我不出来做事,难道你认为他们会把鲁国治理得更好?鲁昭公出走齐国之后,鲁国是更强还是更弱了?我治理鲁国三年,国土扩大,鲁国在诸侯间的威望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不对?善人教民七年,可以戍矣,你说教民七年可以打仗,可我只用了三年,就建设了强大的军队。”
孔丘点了点头说:“公正地说,击退齐国,确实极大地增长了鲁国的士气。”
阳虎紧接着追问:“那么这三年来,你有没有听说过我增加妾室,畜养犬马,敛民致富?”
“没有。”
阳虎抿了一下嘴唇说:“假设你如果从政,是不是也会尽量想办法把鲁国治理好?”
“当然。”
“我们的目的都是要把鲁国变得强大起来。”阳虎笑着站了起来,“我不是要勉强你,只是想请你出来帮忙。”
孔丘沉吟着不说话。阳虎的话虽然有道理,但是自己确实要好好地想一想。
阳虎说:“你每天都在谈仁、礼,怀其宝而迷其邦,可是碰到自己国家需要他的时候,却不肯站出来,用他的经纶救世救国,而在一边袖手旁观,你看这样一个人,可以说他仁吗?”
“不可。”
阳虎接着问:“好!好从事而亟失时,一个人有思想、有办法,才能很大,可以为国家做事,可是每每失去做事的机会,甚至机会找上门来他都不要,你说说看,这个人算是有智慧吗?”
“不算。”
阳虎笑了起来,他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阳虎慢慢向马车走去。他对孔丘说:“考虑好了就来吧。我还要出城办事。”
孔丘看着阳虎的马车离去,他轻轻地摇摇头。他想,是啊,年龄不等人,我也许是真的应该出仕了。
阳虎失手
曲阜城外的大帐中,阳虎正在与公山不纽下棋。
“你为何不去现场呢?”公山不纽惊讶地问。
“一切都安排好了,有下人处理,就可以,我们在这里就等消息吧。”阳虎胸有成竹地回答。
公山不纽戏谑地说:“如若失手,还可逃跑。”
“是的,我在这里还可以看着将军你!”阳虎回答。公山不纽听了,不由得一惊。
羁押季桓子事情,交给了阳越,他派两名卫士将季桓子夹在中间,面如死灰的季桓子不住地哆嗦。突然,车至孟孙府门前,林楚驾车猛然拐弯儿,朝孟孙府门冲去,车至门前,门呼啦及时打开,大车进门,又瞬间关闭。阳越大惊,再追已来不及。
阳越打算越墙抢人,猛然房顶扔下两个圆滚滚的东西,骨碌碌滚到阳越脚下。既而,高墙上方小孔内,箭如雨下。
时过半晌,阳虎放下棋子,叹了口气,说:“看样子我要输了。”
公山不纽将手中的几颗白子轻轻一抛,准确地掷到盒中。说:“博弈之戏,其实我很小就会了。”
阳虎有些气恼地说:“棋输了,我人可能也输了。”
阳虎自言自语地说:“阳越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三家大夫、主公都没有到,想来是出事了。”
这时只听到身后有人笑道:“谁说的我没到?我已经到了。”
阳虎心中一惊,他手中的几个棋子掉落到棋盘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只见孟懿子和子路一起走了过来。
阳虎问:“阳越呢?”
孟懿子笑着说:“现在还没有回来,想来已经是被乱箭射死了。”
帐子的正面走进来了孔丘和鲁定公,公山不狃上前给鲁定公施礼。
阳虎这下心里全都清楚了,所有的这一切,全和公山不狃有关。他一下子陷入了绝望,刚刚站起的身子,又颓然坐下了。
一辆木制的栅栏车停在了外面,两名卫士把阳虎押上了囚车。公山不狃对孔丘施了一礼,说:“多亏你的弟子宰予提醒,我才醒悟。阳虎试图把政,确实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如再跟他谋杀季孙家人,实是陷我与不义。”
这时,林楚和孟孙家的士兵也驾着马车赶到了,车上走下了惊魂未定的季桓子。
阳虎之乱的平定,让鲁定公非常满意,他赏赐了林楚、宰予等有功之士,并封孔丘为中都宰。
阳虎篡权,罪该斩首,然而时隔不久,兵士来报,死囚车竟然神秘失踪,阳虎逃跑了。
救阳虎的不是别人,正是心怀叵测的少正卯。
曲阜城门口的一个小屋里,阳虎端着一碗米粥猛往肚子里灌。
少正卯一脸冷笑说道:“为了救你,我派弟子整整辛苦了一个晚上,阳虎你也真是无情,连句谢谢都没有吗?”
“谢什么,我虽然逃脱了,可我鲁国的心腹全归了你。”阳虎还了少正卯一声冷笑。
“孟孙大夫正在搜城,已往这里赶来。”守城门士兵悄声说道。
“记住,明年我再回来拜祭你。”阳虎连忙起身,对少正卯说完便走。落下一个少正卯傻呆呆站在那里。其实阳越也没有死,带领十几个卫士早已逃出曲阜,去了阳关。
齐鲁会盟
转眼一年过去,鲁国国内平安无事。孔丘任职中都宰,政绩斐然,四方来归。鲁定公十分满意,升迁他为小司空。可后来一想,中都毕竟是小地方,如果用治理中都的办法治理鲁国,效果岂不更好。于是很快地又升迁孔丘为大司寇,主管鲁国的刑讼。
鲁国原本在阳虎强兵政策的影响下,军力大长。现在孔丘又以礼治国,民心归附,鲁国的国力在阳虎兵变之后的一两年内有了显著的增长。鲁国的太平景象和蒸蒸日上无形中给地理相邻的齐国带来强大的震慑。齐国不少官员认为,如果鲁国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对齐国形成重大威胁。晏婴已经年老,近来生病在床,代理国相的黎鉏向齐景公献计:派人到鲁国相约,约于夹谷会盟。表面上是会盟,实际是将兵士扮成莱国的野人,将鲁定公劫持到临淄,让他做第二个鲁昭公。
在鲁定公的后花园里,孔丘拿着齐国送来的竹简仔细地看着。鲁定公高兴地说:“夫子觉得怎么样?夫子治国有方,齐国仰慕得都要归还鲁国土地了。”
孔丘有些忧虑地说:“这里面充满了溢美之词,很多都是夸大的不实之辞。臣不过做了司寇几天,就说臣把鲁国都治理得上下有序,百姓安乐。况且毫无来由,齐国怎么会想起归还郓城呢?臣还是觉得,去自然当去,但是一定要带兵车,有所准备。”
鲁定公也有些顾虑,说:“你说得也是。不过这上面可是说两国国君仿乘车之会故事,不带甲兵的啊。”
孔丘断然地说:“有文事必有武备,还是两手准备的为好。”
季桓子在一旁说:“可是我们鲁国以礼仪信义闻名天下,如果我们带了兵士被齐国发现,岂不会让人家怀疑我们的诚意?”
听季桓子这样说,孔丘沉思着拿不定主意。
“郓城是个好地方啊!”鲁定公站起来说道:“寡人心意已决,不带兵车,寡人带几个从人傧相即可。”
看到鲁定公已经做了决定,孔丘说:“如果是这样,臣请随主公前往,为主公傧相。”
会盟的处所在齐鲁交界夹谷的一块空地上,这里山花烂漫,溪流淙淙,绿草茵茵,一片好景致。仆从抓来了一只大雁,在大雁的脖子上割了一下,血便汩汩地流了出来,滴入了盛满酒的两只酒爵内。齐景公微笑着拿起其中的一爵对着鲁定公说:“齐鲁两国,唇齿相依,历代姻亲不断。近来听说鲁国大治,不胜喜悦,特约您到这里,会盟是假,游山玩水是真。”
孔丘拿起案上的另一酒爵恭敬地交给鲁定公。鲁定公拿起酒爵,笑着说:“难得您有如此兴致,希望两国从此能世代交好。
两人各自一饮而尽,然后笑着坐回自己的座位。
此时,音乐声起,节奏十分散乱,孔丘不禁皱起了眉头。只见一些齐国野人跑了进来,跳着奇怪的舞蹈。装扮奇形怪状的齐国士兵嘴里叨念着什么,在距离鲁定公不远的地方手舞足蹈。
孔丘觉得有些不对劲,用身体护住鲁定公,他也已经认出了曾在高昭子家供职的黎鉏。
黎鉏看孔丘挡在了鲁定公的前面,觉得情况不妙,举起手正要击掌。这时只听孔丘大声喝道:“都给我退下去!”
跳舞的人并不理睬,仍然向鲁定公围拢来。孔丘猛地跑到奏乐的地方,抬腿踢翻了乐师的乐器。音乐声止,所有在场的人都愣在了那里。
齐景公刚想要说话,黎鉏示意由自己来说。他走上前一步,说:“司寇这是什么意思?早听说夫子以精通礼仪著称,难道这样,就是鲁国的礼仪吗?”
孔丘凛然地说道:“齐鲁两君友好盛会,不用宫廷雅乐,为什么却用夷狄之音?齐国主公想来不会对这些野蛮人的如此行为觉得很对吧?”
齐景公有些语塞地说:“这些……都是些莱国的俘虏……”
孔丘说:“这就更加不对了,两国国君相见会盟,一群蛮夷的俘虏,难道也有资格来献舞?”
孔丘厉声对那些化妆的野人说道:“还不快给我滚出去!”
黎鉏站起来说:“既然鲁国君臣喜欢宫廷雅乐,那么就请欣赏齐国的宫廷之乐。”
乐声再次响起来。一群侏儒手里拿着小小的刀剑,随着音乐舞蹈而出。这时侧面的帐子里又走出了十位美女,站在那里各自舞动起来。鲁定公看到美女,眼睛发亮,他直直地看着。
美女一边舞蹈,一边和侏儒们向鲁定公的座位靠近,带头的侏儒见定公只顾专心看美女,于是举剑向定公刺去。孔丘看到侏儒的刺杀动作,守护不及,只好惊呼:“主公小心!”
只见人影一闪,侏儒应声倒地。鲁国左右司马和子路率兵及时赶到。孔丘暗喜,起身质问齐景公:“不知贵国这是什么意思,还请齐国主公解释。”
忽然,帐帘打开,晏婴颤巍巍地被晏圉搀扶了进来。齐景公忙跑过去一起搀扶晏婴。
晏婴附耳对齐景公说:“田大司马召集军马,齐都恐怕危急。”齐景公马上改变了脸色,做了个手势,齐国的侍从收起了武器。齐景公向前走了一步说:“这次盟会,鄙国多有失礼,请鲁国君臣不要见怪,希望今后齐鲁两国交好,不要再起争端,目前齐国有事,鲁国请出三百乘兵车跟随。”
鲁定公正想答应,孔丘上前一步说:“那请齐国奉还历年占鲁的汶阳、郓城、龟阴三地,鲁国自当跟从。”
齐景公想了想说,我答应你。黎鉏在旁边想要插话,景公一字字地说:“你再说一个字,我就杀了你!”说完与晏婴匆匆走了出去。
孔丘暗自庆幸,十天来的私下打探和精心策划,幸好有惊无险。
失宠鲁国
齐鲁会盟鲁国大获全胜,鲁定公高兴之余,并没有忘记孔丘、子路等人的救驾之功,回国后他立即拜孔丘为相国,封赏众人。孔丘出任鲁相之后,也打算趁此东风,整治鲁国,决定以拆除三桓城墙为突破口,削弱三桓势力,重树鲁国君臣之礼。
殊不知树大招风,位高遭嫉。整日沉浸淫逸享乐的季桓子,对官职不断高升、势力大有超过季孙的孔丘早已心怀不满,如今孔丘要拆城墙,削弱三桓势力,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而那位心怀叵测的少正卯,更为阴毒,在得知孔丘官拜相国后,妒火中烧,这位处心积虑已久国内遍布党羽的官学先生,正在着手谋划着一条颠覆鲁国篡权夺位的毒计。
孔丘带着子路、曾点、曾参、冉求等人检查三桓的城墙,当他们行至费邑时,发现城内竟空无一人。仔细搜寻,才在一个坚固的院子中发现被关押的百姓。百姓们的一席话让孔丘等人大吃一惊,公山不纽已率军突袭都城,声称劫主公,占曲阜。
的确,公山不纽的军队像滚滚的波涛,向曲阜涌来。守城门的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丧命在公山不纽军兵的剑下。
此时的鲁定公正在美女的簇拥之下,欣赏着歌舞,一个满身血污的守城兵士突然来报:“大事不妙,公山不纽造…造…反了!”
定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喝道:“难道他还敢攻占曲阜不成?”
“公山不纽因主公要拆他城墙之故,已攻入大殿,没找到主公,现在正朝此处杀来。”士兵带着颤抖的声音回答道。
季桓子见状,连忙拉定公到季孙家的高台躲避。
定公面对公山不纽的浩浩大军,吓得直打哆嗦。说道:“堕都城的事情,得罪了将军,寡人改主意了,不堕了好不好?”
“主公不必说了,事情都到这步了,难道还可以回头吗?”公山不狃对身后的弓箭手做个手势,示意做好准备。
定公不禁暗暗叫苦,恼恨孔丘给自己惹下如此大祸。忽然,几支飞箭从耳旁呼啸而过,深深扎入身旁的木柱,发出嗡嗡声响。定公下得一阵阵晕眩。
没想到曲阜如此容易得手,公山不纽不禁赞叹少正卯送给自己的锦囊妙计,于是朗声叫道:“堆柴,给我烧!”
定公吓得闭上了眼睛。只听一声声惨叫,公山不纽的几名手下应声倒下。但见孔丘在房上拉弓搭箭,一箭正中公山不纽肩膀。受伤的公山不纽面对如雨的飞箭,不敢恋战,丢下手下的兵士,夺路而逃。
国内叛乱虽然平息,可孔丘发布的堕三桓之城的命令,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心生怒火的孔丘,首先来到他的弟子孟懿子的成邑。不巧却发现齐军压境,兵临城下。只见少正卯正伙同齐国的黎鉏率军向鲁过气势汹汹地逼来。
原来少正卯的篡权夺位计划,就是一边煽动公山不纽叛国,一边游说齐景公伐鲁,欲内外联手,一举灭鲁。然而公山不纽的失手,给了齐军不小的震慑,齐军又不敢贸然出击,无奈撤军。
机关算尽的少正卯终没有逃脱他自设的罗网,命丧孔丘剑下。
孔丘提着少正卯的头颅去见定公。此时的孔丘在定公眼里已不是那个政绩卓著、胆识过人的爱臣了,而是成了一个给主公带来杀身之祸的多事者,孔丘斩杀少正卯,更让定公认为孔丘嫉妒官学轻率杀人。因此鲁定公把所有的怒气和怨恨都发泄到了孔丘的身上。望着定公身边一脸奸笑的季桓子,孔丘一言不发,他清楚,定公的误解,再加季桓子的谗言,自己已是百口莫辩。
正在此时,精挑细选的齐国美女,送至鲁定公面前。定公一见美女,立即眉开眼笑。
孔丘对鲁定公施礼说道:“主公,夹谷之会,齐人居心不良,之后,就是这个黎鉏,还曾带兵犯我边境,今日前来进献美女,分明是要蛊惑主公,齐国对我鲁国,一直有觑觎之心,还请主公千万不要上了齐国的当!”
黎鉏满脸堆笑,说道:“齐鲁误会,早已冰释,此次前来只是听说主公被公山不纽所困,后来知道主公无事,于是就撤军了。”
定公也补充说:“是啊!如果退回去,让齐国主公的脸往那放呢?”
孔丘面对黎鉏的狡辩,怒不可遏,上面欲赶齐人离开。忽然定公的一只鞋迎面掷来,孔丘躲闪不及,正中他脑门,头上的儒冠被击落在地。
“孔丘,你给我滚!”定公气得高声吼了起来。
此时的孔丘如五雷轰顶,他向定公深施一礼,向殿外走去。身后响起了丝竹之声。